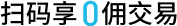摘要
“太阳之下无新事”,通过研究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自大萧条时期以来的历史经验,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已成为常见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操作规模、期限与品种选择等细节则各具特点,可为我国完善国债买卖操作提供借鉴。
从规模来看,在QE时期(如21世纪的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购买的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均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差异较大;而在非QE时期,购买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多数不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不超过7%。
从期限来看,通常遵循两种模式:一是与国债市场期限结构、投资者偏好相匹配,以尽量减轻对利率曲线的影响;二是以调控利率曲线为目的,购买特定期限国债,以压低对应期限的利率水平。
从品种来看,央行通常以购买国债为主,但澳联储也购买了地方债。截至2025年10月底,澳联储的国债与地方债持有比例约为“80%对20%”。
此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购买国债普遍形成了提前公告机制,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滑国债操作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在我国,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在短期有助于投放流动性并引导收益率曲线,在中期有助于建立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体制机制,在长期有助于逐步构建“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
规模方面,从不过度影响市场利率的角度出发,美联储经验显示每购买相当于1.5%的美国国债余额的国债规模,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下降约15bp。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持有至到期投资较多,收益率可能对购债规模更加敏感。从非QE时期的经验值出发,海外央行购买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多数不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不超过7%,静态下对应的国债持有规模分别为9.4万亿元和2.8万亿元,而目前人民银行国债持有量约2.1万亿元,存在提升的空间。
期限方面,我国的期限选择需要考虑维持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和合理的净息差水平两重目标。在收益率曲线形态合意时,可以将买入国债的期限向二级市场国债交易期限靠拢,灵活开展全曲线操作。当收益率曲线过于平坦或隐含的息差水平偏低时,则可以通过“买短卖长”等方式着重引导局部曲线。
品种方面,参考澳大利亚联储经验,可考虑进一步将地方一般债纳入公开市场买卖范围,降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
长期来看,各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本国国情,形成了差异化的货币发行制度:欧元区普遍将黄金作为支撑货币发行的主要信用背书;新兴经济体普遍将美国国债作为货币当局的重要资产;美国则逐渐完善依托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模式。我国国债市场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或可从人民银行买卖国债这一工具切入,有序提高通过买卖国债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逐步构建“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一、引言
2025年10月,人民银行公布10月净买入200亿元国债,意味着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正式恢复。无论从持有的国债规模与货币当局总资产、国债存续规模,还是GDP的比值来看,与发达经济体央行相比,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都处于较低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具体来看,人民银行持有国债占货币当局总资产、国债存续规模、G DP的比例分别为4.6%、5.5%与0.2%,大幅低于国际发达经济体(选取本文重点研究的美日英澳四国)的平均值68.0%、37.6%和33.8%。
本文将细致梳理发达经济体买卖国债的细节,从政策目标、操作规模、期限选择到市场影响,在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我国国债买卖操作未来的走向。
 二、国际经验:美联储买卖国债
二、国际经验:美联储买卖国债
2.1 应对大萧条
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大相同点在于,美国国会和民众都期盼美联储能够介入国债公开市场,以期逆转经济颓势(Bernanke and James,1991;Bordo and Sinha,2016;Bordo and Sinha,2023)。而不同于2008年,美联储在大萧条时期尚未形成独立的货币政策体系,国债操作也处于探索阶段。
在大萧条期间,美联储首次尝试通过买卖国债调节收益率曲线并刺激增长。1932年4月至8月,美联储购买合计11亿美元的中期(Notes)与长期国债(Bonds),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该比例类似于金融危机的第一次QE期间。1932年4月16日,《纽约时报》评论道:“为了摆脱信用紧缩与物价低迷,美联储正在尝试所有中央银行都未曾做过的方法,即控制性扩张(controlled expansion)。”
学术研究也证明,大萧条期间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有效的降低国债利率并提高产出增长率,并且购买中期(Notes)与长期国债(Bonds)的效果更为显著(Bordo and Sinha,2016;Bordo and Sinha,2023);具体来看,在剔除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后,1932年美联储的国债购入行为使得中期、长期国债利率分别下降114bp与42bp。
大萧条的另一项重要影响,在于货币发行的信用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1933年3月,新任总统罗斯福取消金本位制度,再结合1932年2月通过的《1932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 of 1932),美国国债正式被确立为美元发行的信用背书。而在《1932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之前,由于美国国债无法被联储银行用作联储银行券的抵押品,限制了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Bordo et al.,2002)。
货币信用体系变革对经济复苏的影响立竿见影,脱离金本位制的国家得以在弱约束下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1935年为例,金本位与非金本位国家的平均M1增速分别为-6.7%和4.6%。通过实施扩张性政策,非金本位制国家的物价水平也快速得以恢复,逐渐步入经济复苏阶段。

作为小结,美联储在大萧条及后期的国债买卖操作,内在逻辑与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高度一致,均有效缓解了危机高峰期的流动性高度紧张。规模方面,两次购买国债的体量均为当年GDP的2%左右。伯南克在其著作《论大萧条(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也明确指出,美联储在1932年为应对大萧条而实施的国债操作行为,对于QE时代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操作样本。同时,《1932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为美元发行的主权信用模式奠定基础,产生长远影响。
2.2 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20世纪40年代,美联储为满足战争时期的财政融资需求,遵循钉住国债名义利率的操作原则,财政政策的优先级远高于货币政策。
受到罗斯福新政等影响,美国政府的债务赤字大幅提升,国债管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1941年,为实现降低战时的债务压力,美国财政部的方案为:大量注入准备金,压低短期利率,再传导至收益率曲线的长端;而美联储的方案为:通过购买长期国债抑制长端利率,同时应允许短端利率小幅上升以对抗短期通胀(Carlson and Wheelock,2016)。最终,双方在1942年3月达成协议,将短期利率上限钉住0.375%的较高水平,同时钉住其他中长期期限的国债利率。
在1942-1945年的二战期间,美联储配合财政部发债计划,大幅购买短期国债以稳定短期利率;在长端利率方面,由于2.5%的上限与市场均衡水平相近,美联储并未操作长期国债。自1941年末至1945年末,美国国债总额由580亿美元提高至2760亿美元;在同期,短期国债占美联储总资产的比值由接近0%大幅升至28.5%。此阶段的另一重要现象是美联储行为与国债投资者之间的博弈:由于收益率曲线被利率上限钉住,“ride-the-curve strategy”在投资者间盛行,加剧了对于短期国债的抛售,因此美联储也被迫大量购入以平抑利率波动(Garbade,2020)。
直至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7月,财政部才同意取消短期国债的利率上限。而由于短期利率市场化但长期利率上限仍被钉住,市场投资者自1947年底起开始抛售长债,美联储则被迫大量购入,以稳定长端利率(Garbade,2020;加贝德,2024)。仅在1948年,美联储便将长期国债(Bonds)持有量提升80亿美元,同时短期国债(Bills)头寸减少60亿美元。根据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美联储持有长期国债的比例迎来明显上升,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值从1947年11月底的2.0%提升至1950年6月底的14.3%,而短期国债的比例则相应下降。
随着二战后经济走向复苏,长期利率上限逐渐成为遏制通胀的主要掣肘,倒逼财政部与美联储重新讨论财政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配合。1951年3月签署的“财政部-美联储”协议(1951 Treasury-Fed Accord)标志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取得突破,不再承担战时对国债名义利率的维持义务。该协议的核心目标为“通过债务管理与货币政策,确保国债按照政府需求成功发行”,体现出财政与货币当局的配合导向。同年4月,双方协商取消了2.5%的长期利率上限,国债长期利率也随之迅速突破该数值。
作为小结,在二战与战后初期,美联储为配合财政部的发债计划与国债利率上限规定,通过大量买卖国债平抑收益率曲线波动。但随着战后经济快速复苏,美联储的独立性逐渐确立,不再以配合战时债务融资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唯一纲领,以国债操作为切入点,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进入新阶段。
2.3 后金融危机时代
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美联储主要依托于“稀缺准备金(Reserve Scarcity)框架”,国债买卖规模较小,传导路径为“美联储国债买入(卖出)——卖方(买方)账户准备金余额上升(下降)——准备金整体规模上升(下降)”。同时,美联储基本参照存量市场的期限结构开展购买操作,尽量避免对收益率曲线造成冲击。
为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在美国国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市场迅速介入,主要利用大规模资产买入(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即LSAP)这一手段,通过多阶段QE释放流动性。在2008年至2014年的QE1、QE2、OT(扭曲操作)与QE3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也由0.9万亿美元大幅上升至4.5万亿美元。
在操作特点方面,自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国债操作在不同期限上“有进有退”,并且注重将国债买卖的效应传导至市场利率。例如,在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期间,美联储的“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即OT)主要通过购买6670亿美元的6至30年期中长期国债,同时出售相同规模的3年及以下期限的国债。一方面,通过调整短期与中长期国债的期限结构,在不调整短端政策利率的前提下,引导长端利率降低;另一方面,“扭曲操作”有效引导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由QE2初期的4.6%,逐步下降至OT结束时的3.4%,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同期就业率等数据也迎来回暖。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也建立了国债买卖的提前公告机制,以稳定市场预期。由于美联储买卖操作是通过纽约联储与其一级交易商开展买卖,纽约联储的公开市场交易台会在每月第9个工作日披露该月计划操作的金额、日期、品种、到期期限、单次购买上限等信息,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平抑相关操作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回到当前市场,持有规模方面,截至2025年第二季度末,美联储的国债持有量约占国债总规模的14.2%,占比低于海外投资者(34.5%)与共同基金(17.9%),但明显高于我国2025年9月末的5.7%。期限结构方面,截至2025年10月底,美联储持有国债中占比较高的期限为10年以上(比例约37.8%)和1-5年(比例约33.7%),呈现多元化分布。
 三、国际经验:日本央行买卖国债
三、国际经验:日本央行买卖国债
3.1 FTPL理论:为何日本央行重视
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前行长白川方明在著作《动荡时代》中指出,中央银行和财政的关系已成为日本等国设计货币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而从日本国情出发,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即FTPL理论)[1]得到了日本政府重视。该理论将国债市场与财政行为相结合,能够在货币政策面临零利率约束时,有效评估财政政策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为FTPL理论做出重要贡献:在这一框架下,若果居民预期持有国债价值高于未来财政盈余折现值,则将增加消费,刺激物价;相反,如果国民预期未来将大规模减税或社会保障开支增加,即财政盈余缩减,则总需求也难以提振,物价水平维持低迷(Sims,1994;Leeper and Sims,1994;Sims,2011)。
FTPL理论勾勒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种蓝图。在其框架中,通常假定中央银行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其确定的物价水平下,政府调节税收、社保等财政政策,确保财政盈余折现值与国债价值相等,与货币当局共同维持物价稳定。因此,西姆斯提出,可以将未来的消费税征收方案、社保支出方案等与通胀目标挂钩,从而通过通胀弥补财政赤字(Sims,1994)。上文研究的美联储在20世纪40年代的操作,则是FTPL理论的反面案例:自二战爆发至1951年Accord事件,在国债利率上限被钉住的约束下,美联储扮演着无限偿还财政部借款(即国债)的角色,独立性较低,对于物价的控制能力较弱,因此难以应用FTPL理论。
3.2 日本YCC时代
当理论映射现实,在白川方明请辞后,日本央行在黑田东彦时代开启收益率曲线调控(Yield Curve Control,即YCC),成为央行买卖国债的又一次大规模实践。而白川方明却因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的保守政策,至今仍饱受争议。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当日本在2013年启动QQE后,日本内阁府官员借鉴FTPL理论,结合日本国情,认为可以通过YCC避免大规模财政政策引发的总需求缩减等“挤出效应”(即利率上升导致总需求下降),以实现财政政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的效应发挥(永滨利广,2016)。
日本央行在2016年11月启动YCC后,买卖国债进一步被确立为调控利率曲线的主要工具,日央行对国债的持有规模逐渐上升。在国债市场中,日本央行的持有比例从2015年底的31.4%,显著上升至2017年底的43.2%,而银行与保险机构的持有比例则相应下降。而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下,日本国内总需求也得以走出金融危机时期,逐渐恢复。
买卖国债的期限选择方面,日本央行在操作上较为多元,从2年期到40年期均有覆盖。根据日央行2025年6月发布的《购买日本政府债券提纲》(Outline of Outright Purchases of Japanese Government Securities),当前购买国债规模与频率正处于缩减阶段,其中10年期以下国债的购买次数由先前的每月4次下调至每月3次,而“10-25年期”和“25年期以上”的购买次数仍维持每月3次与2次。
经过21世纪以来的多轮QE和QQE(包含YCC阶段)后,当前日本央行已成为日本国债的最大持有方。根据日本财政省披露,截至2025年6月底,日央行持有约50.9%的日本国债,第二位为银行与保险机构(33.9%),随后为海外投资者(6.5%)与日本国内社保基金(6.1%)。 四、国际经验: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
四、国际经验: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
4.1 英国央行
英国央行(即英格兰银行)买卖国债的一大特点,在于审时度势的选择操作规模与期限。以2022年9-10月的买入国债操作为例,在英国政府9月23日宣布“迷你预算”的大幅减税方案后,市场反应较为激烈,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单个交易日内上行110bp,而持有大量国债的养老金机构被追缴抵押品,流动性格外严峻。随后,英国央行果断宣布自9月28日起,大规模购入20年期及以上国债,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此次“救市”之所以选择长期国债,在于持有大量国债的英国养老金机构采用的是负债驱动型投资(Liability-driven Investment),而长期国债与养老金机构负债端的久期相匹配,从而实现“资产负债管理”(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即ALM)。自此次救市以来,英国央行的国债持有量也逐渐下降,实现“有进有退”。
货币信用体系方面,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渐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途径之一,占据中央银行购买资产的90%以上。而在金融危机前,英国央行主要通过逆回购等短期操作实施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间流动性。当前,英国国债主要包括传统金边债券(Conventional Gilts)、通胀挂钩金边债券(Index-linked Gilts)和国库券(Bills),截至2025年9月底的占比分别为73.5%、23.8%与2.7%。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方面,英国政府成立债务管理办公室(Debt Management Office,即DMO)专门负责债务管理,并与英国央行之间就债务融资成本等问题密切协调。根据DMO的2025-26财年报告,英国债务管理强调与货币政策相配合,以实现政府长期债务融资成本最小化为主要目标(to minimize the costs of meeting the government’s financing needs)。而在货币当局方面,英国央行也会按季度披露国债购买情况(Asset Purchase Facility Quarterly Report),提高国债操作透明度。
4.2 澳大利亚联储
澳大利亚联储(以下简称澳联储)购入政府债券的一大特点,在于债券品种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也包括地方州政府发行的债券。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底,澳联储持有的政府债中约79.4%为国债、约20.6%为地方州债券。在地方州债中,澳联储对六大州政府的债券均有持仓,其中约78.9%的持仓为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三大经济重点地区的州政府债券。
针对国债买卖的具体操作方面,澳联储同样在二级市场大规模购债,但期限以3年期国债为主,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宏观政策主要以平抑中短期冲击为导向,重视中期利率水平。以2020年11月澳联储启动的政府债购买计划(Program of Government Bond Purchases)为例,针对3年期国债利率实施国债购入,控制在0.25%左右。当3年期国债利率相对稳定后,澳联储在2022年2月宣布退出这一计划,实现“有进有退”。
货币信用体系方面,澳元发行是澳联储在锚定国债的基础上结合再贷款情况,并且澳联储也会采取公开市场国债买卖的途径影响货币投放量与利率水平。因此,国债市场与国债管理对于澳大利亚的经济运转也具有枢纽作用。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方面,澳大利亚设立澳大利亚财务管理办公室(Australian Off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即AOMF),负责国债管理工作。为管理市场预期,AOMF定期在官网披露下一阶段的国债发行计划,包括品种、利率、规模、投标日期、交易日期等,同时澳联储在大规模购债期间也相应予以提前公告。根据澳联储官网的货币政策解读,货币当局通过与财政系统的债务管理政策相配合,实施国债买卖操作,调控3年期国债利率水平,以此将经济活动的融资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
4.3 总结:发达经济体央行经验
下表对美、日、英、澳各国央行的买卖国债操作予以总结,从目的、期限、规模、公告四个角度进行对比。区分QE与非QE后发现:在QE时期(如21世纪的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国债买卖常被用于在常规工具穷尽时向市场注入大额流动性,操作规模也相对较大,购买的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均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差异较大;而在非QE时期,国债买卖则被用于辅助战时融资、应对投资者抛售、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等特殊性或突发性事件,效果均较为显著,购买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多数不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不超过7%。整体来看,各国央行会根据操作目标与实际国情,审时度势的选择国债买卖的规模与期限,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普遍形成了提前公告机制,以稳定市场预期,平滑国债操作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五、如何优化:结合国际经验与当前形势
五、如何优化:结合国际经验与当前形势
5.1 操作规模
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对政府债权数据显示,2025年1-10月共减少约6700亿元,而2024年8-12月该科目新增1.35万亿元,两组数据的差值约7000亿元,或可对应2024年央行公开市场净买入国债的未到期余额。随着公开市场买入国债的到期,可通过新一轮操作予以补充。
考虑到当前我国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空间大于美国QE与日本YCC时期,且我国银行间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人民银行购买国债通过国债买卖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急迫性较低,但对于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从以下不同的维度推算购买国债的合意规模。
一是从稳定债券市场的角度出发,合意的国债购买规模应当不过度影响市场利率。通过梳理下表中关于国债买卖如何影响收益率的研究,在剔除QE过程中其他因素影响后,美联储每购买相当于1.5%的2008年底美国国债余额(约1550亿美元)的国债规模,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将下降约15bp(Li and Wei,2013;Gulati and Smith,2022)。2025年10月,我国国债托管余额为39.4万亿元。与美国债券市场相比,我国商业银行是国债的核心投资者,且我国更多商业银行选择将国债持有至到期,使得用于二级市场交易的国债更少,因此,在我国,购买同等体量国债对收益率的影响可能更大。
同时,借鉴美联储等央行经验,人民银行可提前公告季度或月度的国债操作计划,以稳定市场预期。
二是从海外央行购债规模的角度出发,根据上文,在非QE时期海外央行购买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例多数不超过20%,占国债余额的比例不超过7%,静态下对应的国债持有规模分别为9.4万亿元(约占当前人行总资产20%)和2.8万亿元(约占当前国债余额7%),而目前人民银行国债持有量约2.1万亿元,存在提升的空间。
5.2 期限与品种选择
国际经验显示,中央银行通常根据当时的政策目标来决定国债买卖的具体期限。根据上文,中央银行选择购买国债的期限时通常遵循两种模式:一是与国债市场期限结构、投资者偏好相匹配,以尽量减轻对利率曲线的影响;二是以调控利率曲线为目的,购买特定期限国债,以压低对应期限的利率水平。
结合我国实际,从人民银行的表态来看,其国债买卖操作可能需要考虑收益率曲线形态(维持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和避免净息差过低的目标。
若要维持向上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则需要根据收益率曲线的变化灵活调整购买期限。当曲线形态合意时,可考虑将买入国债的期限向二级市场国债交易期限靠拢。当前我国存量国债剩余期限在3年及以下的占比约44%,但年初至今的成交额占比仅23%,体现出市场交易中长期国债的活跃度较高。整体来看,当曲线形态合意时,转向多种期限灵活操作可减轻对利率曲线形态的影响。当曲线形态需要优化,如期限利差偏窄时,则可能出现“买短卖长”,引导曲线陡峭化的操作。参考人民银行工作论文,我国短端利率对中长端利率的影响程度较国际主要国家低25%左右(马骏等,2016),也为我国同时引导收益率曲线上不同的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若要避免净息差过低,则需要保持国债收益率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之间合理的利差,在利差过低时暂停净买入。
那么,什么样的收益率曲线形态和利差水平是合意的?从曲线形态来看,在2024年8-12月“买短卖长”期间,10年期与1年期国债利差从70bp逐步下降至30bp左右;而在2025年10月底重启国债买卖时,10年与1年期利差约50bp。从利差水平来看,在2025年1月停止国债操作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7天逆回购利率之差、与国有大行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之差分别为13bp、53bp,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而到10月底重启时,相应利差已扩大至约40bp、85bp。
品种方面,可考虑进一步将地方一般债纳入公开市场买卖范围。根据国际经验,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均可作为央行公共市场买卖的操作选择。以澳大利亚为例,截至2025年10月底,澳联储的国债与地方债持有比例约为“80%对20%”。澳联储面向地方州政府债券的买卖操作,对于平稳地方债市场也产生积极作用。结合我国实际,当前地方债发行规模较大,并且一般债信用风险很低,人民银行或可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地方一般债,降低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
5.3 制度建设:成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抓手
根据中央顶层规划,结合国际经验,人民银行国债买卖操作将成为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的重要抓手。202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潘功胜行长在金融街论坛的演讲也表示,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是“增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协同的重要举措”。
根据《2023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三,从人民银行的角度出发,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有三大途径:(1)支持政府债券发行,人民银行在政府债大规模供应时做好流动性安排;(2)熨平日常财政收支影响,人民银行做好对财政收支变化的跟踪预判,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对冲,保证银行超储余额合理充裕;(3)协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手段,有效引导银行信贷支持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同时完善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配套机制。聚焦于国债市场,参考人民银行工作论文的研究,货币当局可与财政部加强沟通,一方面熨平国债发行引发的潜在利率波动,另一方面使得国库现金管理与公开市场操作相协调(马骏等,2016)。
借鉴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国债买卖经验,稳定通胀预期对于央行调节收益率曲线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也是各国央行介入国债买卖的重要参考。根据上文的美联储研究,自大萧条至后二战时期,美联储始终将通胀情况作为介入国债买卖的信号指标;而以日本央行为例,2016年启动YCC后开始以固定利率购买国债,但同时提出“通胀超调承诺”(Inflation-overshooting Commitment),即通过国债操作等确保货币政策宽松,直至通胀达到并稳定在2%的目标值(Kawamoto et al.,2025)。同时,可参考美联储、英国央行与澳联储经验,可依据通胀率、资金面等市场形势做到“有进有退”,以对应潘行长表述的“灵活双向操作”。
对应我国当前形势,物价水平正处于小幅回暖阶段,整体通胀风险可控,对于央行介入国债操作的约束较小。因此,从机制建设的角度出发,可以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作为切入点,加强财政系统与货币当局针对国债发行、国库现金管理等领域的协调沟通,最终实现财政、货币政策协同的目标。
5.4 逐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
从长期视角出发,根据潘功胜行长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的署名文章,我国将“逐步构建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而本文研究表明,人民银行买卖国债可成为我国逐步构建这一机制的重要抓手。
根据前文研究的美国大萧条时期经验,在《1932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推动下,美国完成了第一次由金本位向主权信用货币发行模式的转型,有效推动经济走出颓势(Bernanke and James,1991;Bordo et al.,2002;Garbade,2020;李扬,2021);英国央行自金融危机以来,也将基础货币的主要投放渠道由短期操作转向国债市场。
从国际对比的角度,各国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本国国情,形成了差异化的货币发行制度。(1)以欧元区为例,普遍将黄金作为支撑货币发行的主要信用背书,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德国、法国、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占储备资产比例分别为80.3%、75.3%与75.2%;(2)以新兴经济体为例,普遍将美国国债作为货币当局的重要资产,但近年来随着黄金的抗风险等价值凸显,黄金储备占比也逐渐提高;(3)美国则逐渐完善依托主权信用的货币发行模式,一方面以美国国债作为信用锚定物,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另一方面则提高美国国债市场的全球化水平,强化美元的国际地位。
结合当前我国发展,国债市场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因此,或可从人民银行买卖国债这一工具切入,通过不断优化国债操作的期限、品种、方向等维度,有序提高通过买卖国债投放的基础货币规模,逐步构建“短中长期搭配、有中国特色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与此同时,依托我国稳健的主权信用,实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目标。
参考文献
1. 白川方明,裴桂芬等译,动荡时代,中信出版社,2024年,414-421。
2. 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陈剑译,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信出版社,2022年,8-27。
3. 肯尼斯·加贝德(Kenneth Garbade),林谦译,美国国债市场的诞生(Birth of a Markets),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238-263。
4. 李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一个研究提纲,金融评论,2021年第2期。
5 马骏,洪浩,贾彦东等,收益率曲线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2016年。
6. Bernanke, B., & H. James, Second Chapter: The gold standard, deflation. Financial Markets and Financial Crises, 1991, 33.
7. Bordo, M., & A. Sinha, A lesson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that the Fed might have learned: A comparison of the 1932 open market purchases with quantitative easing. NBER Working Paper, 2016, No.22581.
8. Bordo, M., & A. Sinha, The 1932 Federal Reserve open‐market purchases as a precedent for quantitative easing,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23, Vol.55, No.5, 1177-1212.
9. Bordo, M., E. Choudhri, & A. Schwartz, Was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feasible during the Great Contrac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Constrai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2, Vol.39, 1–28.
10. Carlson, M., & D. Wheelock, Interbank markets and banking crises: New evid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ac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Vol.106, No.5, 533-537.
11. D’Amico, S., W. English, D. López‐Salido, & E. Nelson, 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mes: rationale and effect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2, Vol.122, No.564, 415-446.
12. Garbade, K. Managing the Treasury yield curve in the 1940s, Staff Reports, 2020, No. 913.
13. Gagnon, J., M. Raskin, J. Remache, & B. Sack, Large-scale asset purchases by the Federal Reserve: did they w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11, Vol.17, No.1, 41.
14. Greenwood, R., & D. Vayanos, Bond supply and excess bond return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4, Vol.27, No.3, 663-713.
15. Gulati, C., & A. Smith,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Fed's balance sheet: effects and challenges,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2022, 59-84.
16. Hamilton, J., & J. Wu, The effectiveness of alternative monetary policy tools in a zero lower bou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2, Vol.44, 3-46.
17. Hanson, L. K, United States vs. International Impact, The New Faces of American Poverty: A Reference Guide to the Great Recession, 2014, 351.
18. Kawamoto, T., J. Nakajima, & T. Mikami, Inflation-overshooting commitment: an analysis using a macroeconomic model, Oxford Economic Papers, s2025, Vol.77, No.1, 213-233.
19. Krishnamurthy, A., & A. Vissing-Jorgensen, The ins and outs of LSAPs, Kansas C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2013, 57-111.
20. Leeper, E., & C. Sims, Toward a modern macroeconomic model usable for policy analysi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4, Vol.9, 81-118.
21. Li, C. & M. Wei, sssTerm Structure modelling with supply factor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s Large Scale asset purchase progra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2013, Vol.9, No.1, 3–39.
22. Sims, C. A., A simple model for stud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rice level and the interaction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Economic Theory, 1994, Vol.4, No.3, 381-399.
23. Sims, C. A., Step on a rake: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in the inflation of the 1970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1, Vol.55, No.1, 48-56.
24. Swanson, E., Let's twist again: a high-frequency event-study analysis of operation twis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QE2,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1, Vol.1, 151-188.
25. 永濱利廣,話題のFTPL(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とは,第一生命経済研レポート,2017年3月。
注:
[1]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论,即物价水平主要由财政政策决定,而非货币政策。
注:本文来自兴业研究发布的《央行国债买卖——当全球史映射我国现实》,报告分析师:张伟康、郭于玮、鲁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