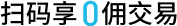【财新网】(记者 周东旭)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关于这一领域如何更好地竞争和创新也越来越引起广泛关注。在数字经济时代,究竟应当沿用比较宽松的监管思路,还是采用较强的监管,仍存争议。
6月16日,《比较》编辑室、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和清华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与创新”研讨会,政策制定者、学界专家和企业代表对上述问题予以探讨。
竞争与创新的平衡
如何维护竞争与创新的平衡,一直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课题。天津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于立以数字音乐为例,提出“保(保护知识产权)反(反垄断)兼顾”理论。
于立介绍,不同于你有我无关系下的稀缺公用品,数字经济时代的很多内容,边际成本等于零,你用了并不影响别人用,当然,知识产权同样要受到保护,没有付费或未进入俱乐部就不能随便使用,他称之为不争用但可限用的共享俱乐部产品。
对于这类产品,于立认为存在着两类悲剧:一类是反公地悲剧,一类是准公地悲剧。所谓反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过度,导致无法有效利用这类产品为社会带来福利;所谓准公地悲剧,就是对这类产品的专利或产权保护不利,导致研发和生产投入不足。他将这两种悲剧现象归纳为“第三象限新公地悲剧”。他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对知识产权或版权,尤其是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相对保护不利的情况下,创新激励不够。
“产业不等于市场。”于立以数字音乐为例,从产品到市场,至少可分为三种,即数字音乐作品、数字录音制品、数字网络传播。所以,“保反兼顾”意味着对应数字经济不同阶段的知识产权,应该有不同的定位,比如原始创新要“高保低反”,对于下游可以“高反低保”,中间环节则需要合理推进。
在于立看来,数字产业不同于一般的产业,法律要保护竞争关系,至少应遵循三个原则,比如,版权保护期限与创新程度成正比,尤其是对于原始创新要加大保护。版权保护的数量与授权期限成反比。网络传播权竞争优先,保护应该主要集中在上游,而不是在此。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王晓辉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尤其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引起重视。“过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强调的是专利保护,实际上对商业模式的保护确实不太重视,很多小公司的商业模式很容易被复制,很容易被山寨。”
王晓辉强调,“对于大型平台企业在颠覆式创新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应该予以肯定。不过也要对它们利用资本力量阻碍商业创新的可能引起警惕。”此外,王晓辉还指出,必须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成果进行全面看待,既要看到它们对GDP的贡献,也要重视它们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对就业的挤压等问题。
竞争新特点
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层出不穷。不过,随着平台兴起,平台型企业的“身份”也变得模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华表示,平台在集中大量数据的情况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类政府的性质。以前企业和政府的界限很清晰,当平台集中大量企业资源和数据,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这些企业的管理者。
在李晓华看来,互联网竞争更多的表现为流量竞争、跨界竞争。随着巨头平台不断开疆扩土,大肆收购,颠覆式创新力量能否出现,已经成为了能否实现竞争平衡的关键。
竞争充分与否,用户转换成本是衡量指标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介绍,用户转换成本比较低,往往意味着价格弹性很大,稍微提价,用户就可能用脚投票,但是,同样可能存在另外的可能,即价格弹性很小,那消费者的选择就很小,甚至等着被宰割。现在的平台一般是多边市场,在某一边市场高弹性的同时,另一边的市场则可能是低弹性的。如何看待那些低弹性市场上的企业行为,需要进行分析。
针对现在流行的一种看法,即监管会损害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刘培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激励相容的适度监管对产业发展,企业竞争力提升可能是有利的,因此完全否定监管并不正确。不过监管的方法和力度很关键。
与会学者基本认同数字经济竞争已经进入新阶段,只是对新在何处,有不同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永伟表示,对互联网企业来说,当前竞争应该是一个告别了低层次的竞争,进入到一个相对高级的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企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和怎么对这些企业或者行业进行监管的问题,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如何监管数字经济
“监管的重点,应该是平台性质和平台行为,不要泛化。平台规模大也好、涉足领域多也好,可能并不是监管的重点。”张永伟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平台型企业是不是做到了严格保护进入平台的中小企业,“有的企业进入平台后,关键看它能否灵活转换,而不是签卖身契。互联网生态应该旗帜鲜明保护中小企业。”第二,对于没有进入平台的企业,是否构成不公平竞争。第三,平台数据,信息和数据应该作为监管的重中之重。
对于“跨界”,王晓辉认为,“巨头没有不做的,什么都做”,巨头公司跨界应该有限度。
刘培林指出,目前有不少人谈到要对平台巨头拆分。在他看来,尽管拆分并不能被排除在选项之外,但对其使用一定要慎重,要看这样做的后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至少在现阶段,它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他强调“即使要进行拆分,也必须保证一条原则,即让企业家的利益在拆分时应该得到保证,至少他们的财务利益应该得到保证。”
关于拆分问题,一位参会的监管机构代表指出,“事实上在最近几十年,都没有对大企业的拆分。而对于针对标准石油的拆分,现在也有不少反思,很多专家认为当时事实上是拆错了。”她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如果一家独大就是一个必然结果,那么拆分的意义就不是很大。相比之下,找出问题的所在,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监管可能更为可取。
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容回避,且呈现出更复杂的多面相。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江飞涛认为,应该调整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服从于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也许很多人会担心竞争形成集中以后的反垄断问题,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中国产业政策往往会更有意的扶植和培育大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大企业一般会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政策,包括管理部门对这些企业在公民隐私、垄断行为和不良行为等方面的作为会有比较强的容忍度。”江飞涛说。
江飞涛进一步解释,竞争性集中之所以显得比较有效率,是因为通过优胜劣汰让有效率的竞争者生存下来。如果只是通过更多优惠政策去培育所谓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它是不是真的有效率,可能就非常成问题了。在数字化时代,无论对于新兴产业、数字产业、互联网产业,对于传统产业也好,产业政策首先还是要服从于竞争政策。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提出了很多新的议题。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平衡好竞争、创新和监管之间的关系,还需学界、业界和政策制定者一起携手研究。”会议主持人,《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在总结时说。